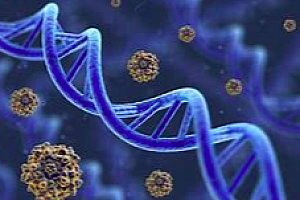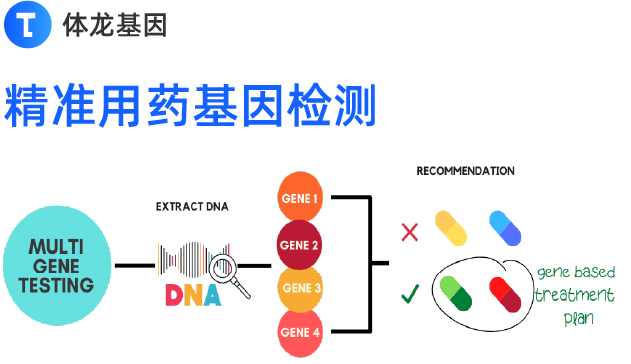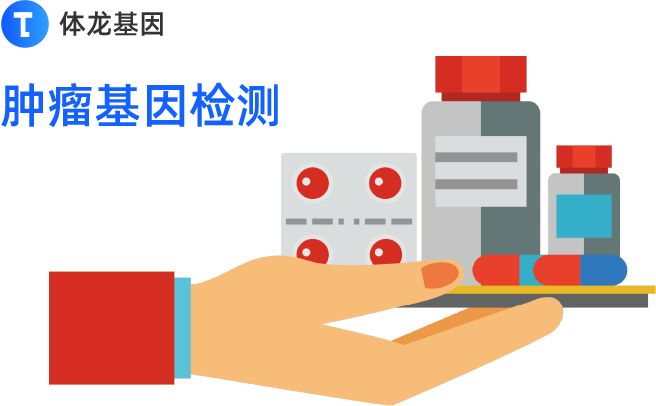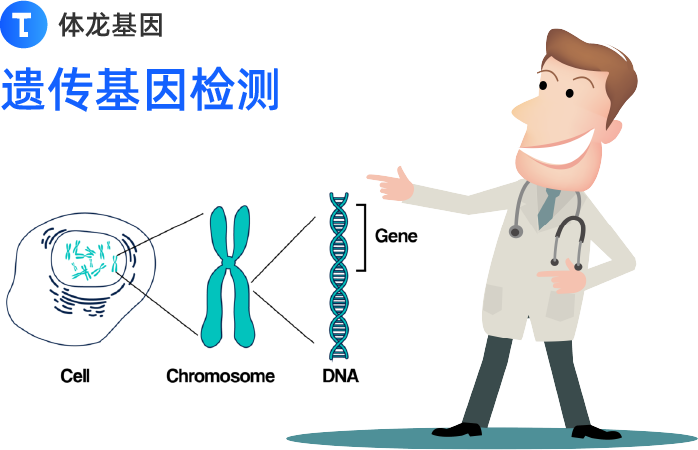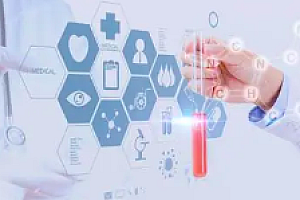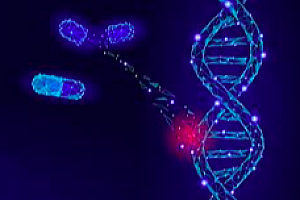1971年,哈佛医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Judah Folkman在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,就这一篇论文,让他后来被列入了诺奖候选人的名单……
论文说了什么呢?Folkman教授在实验中发现,肿瘤可以分泌一种叫做“肿瘤促血管生成因子”(Tumor Angiogenesis Factor,TAF)的物质,虽然还没完成分离提纯,但他相信,对这种物质进行抑制,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抗癌策略[1]!
虽然Folkman教授看到了他梦想中的抗血管生成药走进现实,但他在2008年去世,最终还是与诺奖擦肩而过
许多人都认为,这篇战斗檄文,标志着抑制血管生成,正式被视为抗击癌症的一大策略,没有它,就没有后来叱咤风云的抗血管生成药物。科学界随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探索,对传说中的TAF进行分离提纯、基因测序……
但很不幸,这些努力都跑偏了。许多科学家沿着Folkman教授的研究思路继续前行,但他们却一直没能找到调控血管生成最关键的因子。科研的路从来不好走,而如果向导把后来者带偏了方向,就更难前行了。
而拨乱反正的,是一个研究的领域,本来和肿瘤风马牛不相及的家伙。或者用某句耳熟能详的台词来形容吧:“二营长,把意大利炮拉上来!”
“摸鱼”摸出的曙光
要是按某些公司的用人准则,刚刚加入基因泰克(Genentech)的意大利研究员Napoleone Ferrara,绝对是那种离开除不远的员工——你个刚入职的菜鸟,不专注于自己的本职研究,整天摸什么鱼呢?
而Ferrara心里想的却是:不是哥们不努力,就算咱是学生殖科学的,也不想研究让生孩子不痛的松弛肽(Relaxin)啊,这项目迟早得撞南墙[2]。还不如把自己读博时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呢……
没有诺奖,拿个拉斯克奖也不差啊
幸好,基因泰克是出了名的宽待员工,所以Ferrara能够在周末使用公司的实验室,继续不务正业,探索那些让他如痴如狂的“神秘蛋白质”。它们是从牛的脑垂体里,一种叫做滤泡星状细胞的细胞中提取出的。
滤泡星状细胞当时还功能不明,但Ferrara观察到它们总是分布在血管周围,他怀疑这些细胞参与了垂体血管的生成。Ferrara把这些细胞和内皮细胞混合到了一起,效果立竿见影——内皮细胞开始有丝分裂,生成血管,“上工了”。
看来这些滤泡星状细胞,肯定分泌了什么调控内皮细胞的物质,但这物质是什么呢?只能去分离、提纯、实验才能解开谜团。
Ferrara做好了和这个课题长期死磕的准备,因为早在读书时,很多人就劝他:靠你单枪匹马提纯和搞懂这种蛋白质,至少得十年!但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,他和同事们在基因泰克的实验室完成这些工作,只用了半年多一点儿!
要想人前显贵,也许真得实验室受罪……
1989年,Ferrara把研究发表了出来,他对“神秘蛋白质”的命名很直接,既然这蛋白质是由其他细胞分泌,促进内皮细胞分裂生成血管的物质,就叫它“血管内皮生长因子”(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,VEGF)好啦[3]。
其实早在十年前,就有科学家发现了VEGF,但他们误以为,VEGF是癌细胞分泌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,使组织液渗漏产生腹水症状的物质,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探索,“血管通透性因子”(VPF)的名字也取偏了[4]。
幸好Ferrara没有跑偏,而且他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基因泰克的认可和大力支持,于是在同一年,Ferrara和同事们就完成了对VEGF基因的测序,和另外一组科学家的成果一碰,哈,VEGF就是VPF[5]!
这又引发了一波科研浪潮,科学家们逐渐弄清楚,VEGF其实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,Ferrara发现的是“长子”VEGF-A,此外还有VEGF-B/C/D/E和胎盘生长因子(PGF)和受体VEGFR-1/2/3。虽说复杂了些,但关键点就是VEGF-A。
人丁兴旺的家族,事儿也多……
找到了关键节点,下一步就是验证它的作用了。
1993年,Ferrara的团队发表了用自行研发的单克隆抗体,靶向VEGF的实验效果:单抗和癌细胞一起混到试管中时,并没有抑制癌细胞的分裂,但注射到移植了肿瘤的小鼠模型中,就把不同肿瘤的生长速度降低了70-90%[6]!
这结果既振奋人心,也合情合理。振奋人心,是指抑制肿瘤增殖的良好效果;而合情合理,是因为靶向VEGF的单抗,本来就不会对癌细胞的分裂产生影响,治疗的目标就是控制新血管的生成,掐断癌细胞的补给来源。
就像错综复杂枪炮横飞的战场,不是吗?
经过研究团队的进一步改造后,用于临床试验的人源化单抗诞生了,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贝伐珠单抗(安维汀)[7]。不过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价值,终究还要经历人体临床的试炼。是真金不怕火炼,还是又一个悲情折戟的故事?
突出重围
1997年,已经被罗氏收入帐下的基因泰克向FDA提交了安维汀开展I期临床试验的申请,但随着时间流逝,人们对于抗血管生成药物却不再是翘首以待,甚至可以说不少人已经搬好板凳嗑着瓜子,坐等安维汀栽跟头了。
唔,其实医学界这种对创新和探索的态度也不是啥新鲜事,今年拿到诺奖的癌症免疫治疗,当年不也是在一片冷眼中突出重围的吗?安维汀招来的白眼,倒更多是因为“猪队友”的拖累。大概是因为希望越大,失望越大吧。
二十年前医学界对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期待,就像今天对癌症免疫治疗的热情一样高涨,但在动物实验阶段表现出色,登上过顶级期刊的一些新药,一到临床试验就现了原形,华丽沉没[8-9]。
啥时候我们的临床试验和诊疗,也像医疗剧一样,平板上指点江山呢……
有这样的先例,安维汀的临床试验也免不了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打量。在通过I期试验后,基因泰克同时铺开了针对不同癌症的五项临床试验,但最先达到III期阶段的晚期乳腺癌试验却以失败告终[10]。
虽然在Ferrara这位“亲爹”的眼里,即使是失败也能找到一些闪光点,但毕竟开发药物和组织试验,是要砸下大笔真金白银的,没有无限试错的事情。整个安维汀的项目成败,就全系于一线了——治疗结直肠癌的III期试验。
抗癌药的研发路,是血泪史,也是战场
“冷漠的人,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”,2003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年会上,这项试验的成果给了所有批评声音一耳光:安维汀与化疗方案联合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时,将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4.7个月[11]!
各种历史资料常常会说,多少多少年前的1块钱等于现在的多少钱,那么在2003年,一种能延长患者4.7个月生存期的抗癌药,要怎么换算呢?以奇点糕的看法,它的含金量,不比今天任何免疫治疗试验的数据差。
Ferrara在接到祝捷的跨洋电话时,喝了整整一瓶意大利美酒来庆功[12],这痛饮里面,肯定也有战胜艰难险阻和质疑的喜悦。多年后,拉斯克奖的殊荣就是Ferrara们努力的证明。
2004年2月,安维汀正式获得FDA批准用于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线治疗,成为全球第一种获批的抗血管生成药物,随后FDA又批准了它用于肺癌的一线治疗,以及在肾癌、宫颈癌、卵巢癌和胶质母细胞瘤中的应用[13]。
列队出发,全力抗癌!
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
今天的安维汀仍然魅力不减,排在2017年全球十大最畅销抗癌药之列[14],这倒不是医生和患者恋旧,因为安维汀的价值,仍然是难以取代的,单药、搭配化疗、联合免疫治疗,简直可以说是万金油。
拿肺癌这个争夺激烈的战场来说,专门针对中国晚期肺癌患者开展的BEYOND试验,就充分证明了安维汀的价值,它配合着化疗将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近6个月,比此前在欧美开展的同类试验数据还好[15]!
而且,安维汀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,比如它能配合着EGFR抑制剂实现良好疗效[16],也能和PD-L1单抗Atezolizumab共同取得对肺癌、肾癌一线治疗的成功[17-18],在结直肠癌上,安维汀联合化疗到现在还是一线方案。
在小细胞肺癌、肝癌这些更难攻克的对手面前,大名鼎鼎的PD-1/L1抑制剂也会拉上安维汀做帮手[19],比如在肝癌的早期临床试验中,安维汀配合PD-L1单抗的治疗客观缓解率达到61%[20],已经获得了FDA的突破性疗法认定!
不管是免疫治疗还是靶向药,You’ll never walk alone
不少药企都盯上了安维汀这棵摇钱树,打算趁着专利期满之时,推出生物类似药来抢蛋糕,不过众所周知,一种成熟的药物从研发到生产需要经历各种技术难关,出色的流程,才有药物良好的疗效。
而生物类似药所需要达到的指标,一般还仅限于生物等效性,但结构相似,就代表疗效真的相似吗?一向铁面的FDA,也是在安进的安维汀生物类似物提交了超过600名患者参加的大型临床试验数据后,得到充分证据才亮了绿灯。
但更多时候,生物类似药是在摸着石头过河,就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在审核指标和严格程度上的差异了。这种未知和不确定性,与安维汀使用十几年积攒的数百万患者数据相比,孰优孰劣,恐怕不言自明。
十几年的风云变幻,不过弹指一挥间,而安维汀和抗血管生成药的后辈们,已经在癌症治疗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未来也同样海阔天空。经典的意义,也许就在于永不过时,不管世间,沧海桑田。
扫描上面二维码在移动端打开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