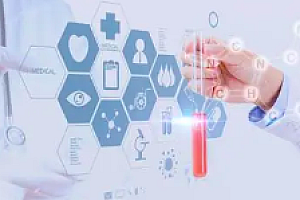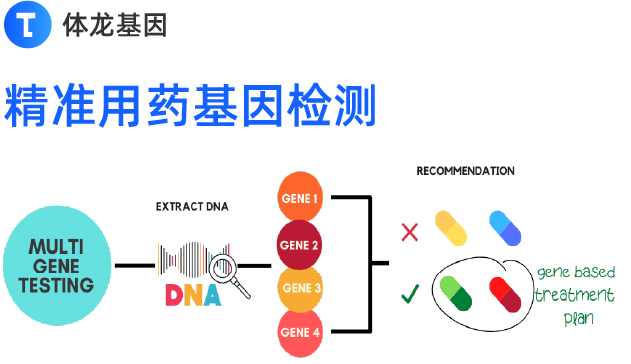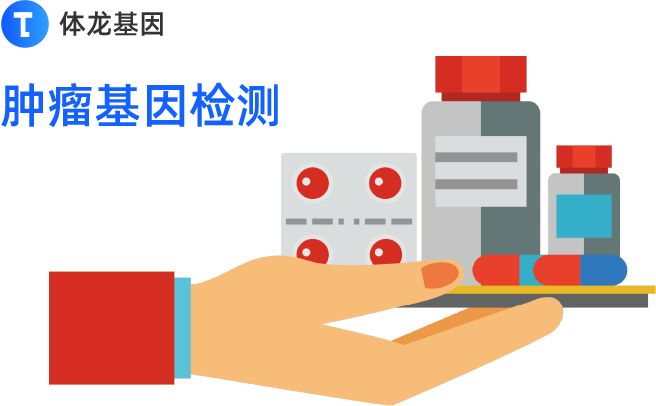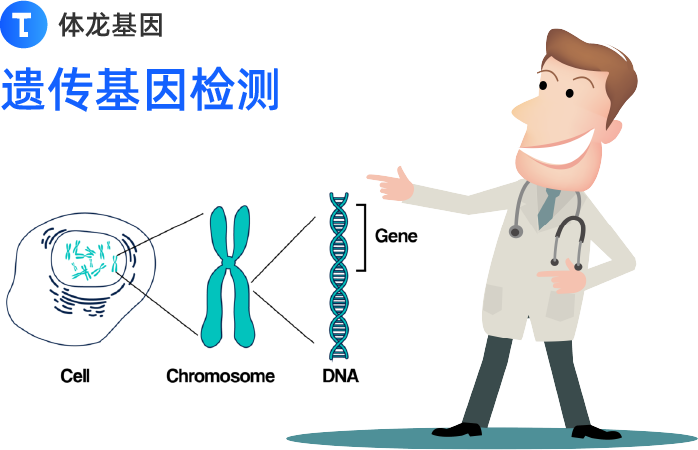11年前,协和转来一个女孩,她的肺、皮肤和骨头全都被病菌啃食到凄烂。为了治病,她在各地的医院查了5年,还被取走了腰椎的一块骨头,但依然没有结果,全国的专家都束手无策。最后,在协和一个接触不到病人的科室里,有个女医生查出了她的病因。2016年,我也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人。他的肺被病菌哨出了各种窟窿,左肺几乎被掏空了1/3。他活着的每一秒,病菌都在不断吞噬内脏。这次,救命的还是那个医生。1那个病人叫小希,一米六五的个子,只有30公斤重。他的肺部CT显示,左右两片肺上布满了小结节,都是被病莲噬咬出的洞。我只看了一眼,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,地板上铺满的水蚁,挤挤挨挨地重叠在一起。见过小希后,我发现他的嗓子里也开始凄烂,血肉模糊。这意味着,病菌先是啃食肺部,现在又腐蚀了喉咙。呼吸科的病,肺肯定都有问题。但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,哪怕暂时不了解,只要病情比较温和,也可以慢慢查。但小希病症的可伯之处在于,它正在急速恶化,既查不清楚,还很凶恶。我不断翻看病历,却找不到一点线索。为了寻求帮助,我拿着他那张极具冲击力的CT,到处请同事给点意见。结果大家看完被啃食1/3的肺部,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医生群里原本还有人分享不常见的CT,探讨惨烈程度,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,全场沉默。走投无路时,我想到了王澎医生。医院有一个“特种部门”——检验科,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“微生物组”,我们都叫“细莲室”。这里的医生能依靠病人的蛛丝马迹,找出致命的病菌。有时,他们一张报告单就能换来病人生的希望。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,王澎医生拥有一个专属代号——“微生物神探”。她每年能亲手验出上百种病菌,成捆的化验单上都签着她的名字。我入职那年,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“细菌室找王澎”。她成了我唯一的希望,所以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港洗液,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,务必交给王澎老师。2检验科在常年不被注意到的偏保角落,门口一片昏暗,只有远处还亮着灯。那天早就过了下班时间,但我惊喜地发现,这里居然还没有锁门。我敲敲玻璃门,灯光下一个皮肤白净、圆圆脸,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头。她就是王澎老师,我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。王老师放开显微镜,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璃片,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。她抬起头看我,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这个病人,非常有意思。”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。她说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,但现在还没十足的把握,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。我使劲点了点头。“小伙子有艾滋病吗?”“没有。”“确定吗?这个很重要。”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,一入院就查过了,除非是处在窗口期,我可以再给他复查一下。紧接着,老师又问了很多问题:他在哪里生活?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?免疫功能正常吗?皮肤有破凑吗?我一一回答,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把我问借了:“吃过竹鼠吗?”往回走的一路上,我禁不住想,艾滋病、吃竹鼠,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感染?第二天查完房,我给王澎老师带来了结果:小希虽然在以“敢吃”著名的省份打工,却从没吃过竹鼠。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文献,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。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,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?王老师表示没有:“我是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确认的,你回去等消息吧。”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。要知道,检验科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注意的一群人,经费有限。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,经费应该也不宽裕,就这样还拿出来给小希额外做工作。尽管如此,我的内心还是越来越不安,小希的情况一直在恶化,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,真的就要扛不住了。当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,王老师总算说:“如果是那种病,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,小希就是第9个病患。之前的8个,几乎都是我诊断的。”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。可我听得越多,越是毛骨悚然。曾经诊断的8个人里,有多达5个人的骨头被啃掉,2个皮肤上“长毛”,甚至最严重的那1个人,大脑里都开始“发毒”。这其中,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和小希的情况最像。311年前,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,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。她总共住过7次院,且数次都能享受到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,没有人不为她的病症所好奇。悠悠和小希一样,19岁那年开始发烧,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,后来越来越严重。父母带着她四处辗转求医,5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,仍然没有诊断清楚,只怀疑是肺结核。悠悠的病症比小希更严重,除了肺里有了空洞,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,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。5年时间里,抗结核、用激素,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。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,怀着最后一线希望,她比小希早8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。诊疗过程异常艰难,医生提取了她的肺、皮肤、淋巴结,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,却仍然没有诊断清楚。最终,我们只能动用“内科大查房”——全院专家集体会诊。这是半年才有一次的顶级待遇,通常只舍得留给最棘手的病人,这次机会给了悠悠。普通内科、放射科、感染科、呼吸科、骨科、血液科、皮肤科、病理科、免疫科的专家们齐聚一堂,讨论很久,最后得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:结核不除外。开始抗结核治疗后,病情缓解了一段时间,但不到一年,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。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烧,后腰上也长出来一个肿包,而且越鼓越大。她再次回来住院时,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多的大小,摸上去还有波动,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争先恐后地涌出皮肤。此时距离悠悠发病,已经过去了6年多,小姑娘被折磨得愈发虚弱,通过检查发现,不仅后腰上,还有臀部、甚至脊柱旁边,也都蓄积着脓液。大家都陷入了困惑,全身这么多脓,真的是结核吗?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,又多了一个身影,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。她把悠悠1年前的标本都重新看了一遍,确实没找到任何病菌。但她坚信,这个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种“狡猾”的病菌,只是因为这种太罕见,所以迟迟没有线素。为了更精准地找线素,王老师亲自未到病床旁边取样,对悠悠皮肤上的大包进行采样,并立刻进行了接种。这一次,病菌没能逃脱。经过层层判断,王老师发现,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菌一马尔尼菲蓝状菌。马尔尼菲蓝状莲很特殊,大部分被感染的人,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。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,还有竹鼠身上,伺机进入人体,这种真会蔓延全身,哨食人皮肤、内脏、大脑、骨髓。第二次内科大查房,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给了悠悠。这一次,王澎老师也参加了。当时场内常有争执,只是她坚定认为,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。专家们反复料酌,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: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,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殆尽。之后减少抗结核药,主要应用抗真的药物。王澎老师还特别叮嘱临床医生,这种真实在太狡猾,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“变形”。在人体内,37度的时候,它是圆圆或者椭圆的形状。而在室温也就是25度的环境下,它慢慢伸出触角,变形成发毛的菌丝形状,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。这种真菌带有一种特征性的玫瑰红色素,可以把培养基或者苗落染成红颜色,所以当你靠近显微镜,就会发现那些样本里,开满了一朵朵“人体政瑰”。这些“玫瑰”最可怕的地方在于,它很容易被误诊为结核。万幸的是,王澎医生终于找到了病菌。经过及时治疗,悠悠有了好转,有了她的经验,后面的病人也没有那么艰难了。当年种种艰难,听得我愣在原地。我那时最想知道的,就是那8个病患的治疗效果怎么样,小希现在还有没有救。4王老师报给了我一个惨烈的数据:“5个病人幸存,3个去世。”这在感染疾病里,已经是极高的致死率。而小希又会是哪一种呢,他能成为第6位幸存者吗?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,雪片般的报告单同一时间飞回了病房。小希咽喉凑烂处取的拭子、咳出来的痰、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、淋巴结组织、肺组织、甚至骨髓液里,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。小希的喉咙、肺、淋巴结,骨髓里,全都开满了“人体玫瑰”。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。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,抗结核、用激素、抗细菌,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。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、撕咬他的血肉。被啃噬得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,活下来的机会茫。我安慰自己,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了,帮我们找到病因。或许现在刹住车,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。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个去世病人的资料,无一例外,都是发现的太迟了。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,但身体也已经被哨噬殆尽。当年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,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,反复住院总数达7次之多才幸存下来。我只能为小希祈祷现在不算太晚。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,王澎老师依旧向我热情地介绍这个病菌。我看着她,只觉得这种认真的样子,让人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很快,我回到小希的病房,准备了抗真菌的药物。这个药物不便宜,小希的父母陷入了两难。他们先用便宜的药物试了试,但副作用差点让小希送了命。这个小插曲让所有人心里一惊,他的父母也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。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,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,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。并停掉了之前的5个抗结核药物,有食欲了,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,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。父母高兴坏了,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好转的速度太快,我怕前功尽弃,再出现什么么城子,也顾不上床位周转率了,咬牙又留小希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。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,体重也增加到了80斤,一颗心才渐渐安稳下来。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,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CT,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“水蚁”已经变淡了一些,虽然那些被哨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,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。这个孩子之前经历了太多病痛折磨,现在终于苦尽甘来。出院那天,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项。小希跟在父母身后,冲我挥了挥手。很快,我再次来到检验科,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。她很开心的样子,问我是不是真的,并且很快就记了下来:“实在是太好了,这是第6个活下来的!”她说自己正在积搂资料,想编写一本真的图谱,到时候也把小希写进去。这样更多人就能认识罕见的真菌,不至于两眼一抹黑,在治疗上走太远的弯路。她还跟我讲了很多未来的愿景,突然,她停了下来,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:“唉,想做的事情太多,时间实在是太少了。”即使心细如我,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。小希出院那半年,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,只是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。几次接触过后,我才明白,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:“细菌室找王澎”。5王澎老师实在太热爱检验病菌这门手艺了。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,再忙也不拒绝,有空就埋头对着显微镜。大多数时候,病原不会满眼都是,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地毯式搜索。这是个良心活儿,曾经有个病人,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,到我们医院以后,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。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的时候,她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么一根小小的菌,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。”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,仅隔着一条街,方便她往医院跑。我有时候甚至会清想,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,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。对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,常人或许很难理解,可我总觉得熟悉。在协和,每天都能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护车,送来的病人往往走投无路,把这里当作最后的希望。作为医生,这种时候,我们总会不由自主想要投入全部。王澎医生是最典型的,她几乎将自己全部时间投入到研究病菌上,用近乎狂热的态度追捕病人身上的病莲。科里领导照顾她,减少了她的工作量,还让她中午回家午休。但王澎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,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,还有好多真等着她去记录。她依然忘我的工作,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。那一声“细菌室找王澎”,依然每天在各个科室响起。6只是好景不长,有一年的冬至,群里突然发起了王澎老师去世的消息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,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,真有什么事,肯定能及时抢救。可噩耗最终被证实,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情,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。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,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。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,希望她能养好身体,同时作为单亲妈妈,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。她却越来越忙,时间太少,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。大家看到的,仍然是那个任何时候、哪怕再小的大夫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,都笑眯眯答应、随时伸出援手的她。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,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还有最后那个,家距离医院急诊只有不到100米,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她。而她的女儿,年仅9岁。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,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,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。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,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。从一个大专毕业、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,用了20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“微生物神探”。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: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,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,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玻璃片。我依稀记得,照片旁边的一句话,“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。”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,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。我第一眼都差点没认出他来,这个留着分头、有点帅气的小伙子,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、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少年,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。小希看到我,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林医生,对不起,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,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。”看他恢复得这么好,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,很想问问他,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,才能让你活下来的王医生吗?然而直到这时,我才突然意识到,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,检验科的王医生,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。在我们医院,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,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。唯独检验科,墙上干干净净。其实这也不难理解,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,打针的护士,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。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,他们却从未不曾留意过。作为医院里的“特种部门”,她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,战场在显微镜下。这是群没有锦旗,没有鲜花,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,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。给小希看完病,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:“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,就是给你找到真的那个人,她现在已经不在了,但你一定要好好的,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。”“哪个王医生?”“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,最下面一行那个王医生。”怕他不好理解,我又加了句,“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”。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,只能保持沉默。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,于是不再讲下去,只是加了他的微信,说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。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,但小希不一样,我想看看他未未的生活,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师的延续。小希默默点头,拿笔记下医嘱,随后准备离开。只是走到大门的时候,他突然停住,说了一句“谢谢”。如果我没记错,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。7送别王澎老师是在一个冬日早晨,天刚蒙蒙亮,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。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八点,每当我们送别战友的时候,通常都会安排在清晨7点钟。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,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,站在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。王澎老师白大衣的队伍越来越长,我再一次回头张望,居然在队尾看到我们科一个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。我赶忙能过去搀扶着她,您怎么也来了?她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,只是看了朋友圈,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。“她是有大爱的人,我要来送她。”长长的几百人的送别队伍里,只有同事,没有一个病人。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:“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,感谢您赋予她新生。她安好,您却走了,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。”我转头看向同事们身穿白大褂,聚成的白色长龙,突然有些释然。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。检验科的医生,更像是幕后的英雄。他们不会直接接触病人,只会留下化验报告单角落里,那个不被人注意的签名。这是一个聚光灯照不到的岗位,甚至没办法听到病人的一句谢谢,而王澎医生的选择是滤尽全力地寻找病菌。王澎医生的妹妹告诉我,她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,常常会用手去触碰。那是她整日在显微镜下寻找线素,被目镜磨蚀的印记。直到她离开的那天,眼皮上依然还有感染。大家总说,协和是病人和死神之间隔着的最后一道门。但这道门,也是由很多不被人关注的医生撑起来的。或许到了这里,我们唯一考虑的,是怎样圆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毕竟,当自己可能是别人最后的希望时,我们不能有一丝懈意。我们也习惯了没有一丝懈意。我为有王澎医生这样的同事感到自豪。有关澎医生:令人动容!两位协和医生间的生死送别……王澎,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,2016 年 12 月 21 日早晨因突发急病,医治无效,永远离开了我们!年仅 40 岁,12 月 23 日(周五)早晨 7:15 将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楼地下二层告别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王澎,中国微生物学、真菌学青年专家,致力于微生物事业和公益事业。据知乎“林大鼻医生”的回答,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,本文有删减,北京协和医院供图
(责任编辑:dawenwu)
协和医院的“微生物神探” ——纪念王澎医生
6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