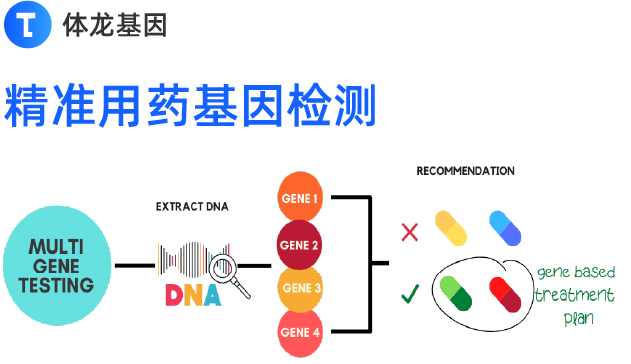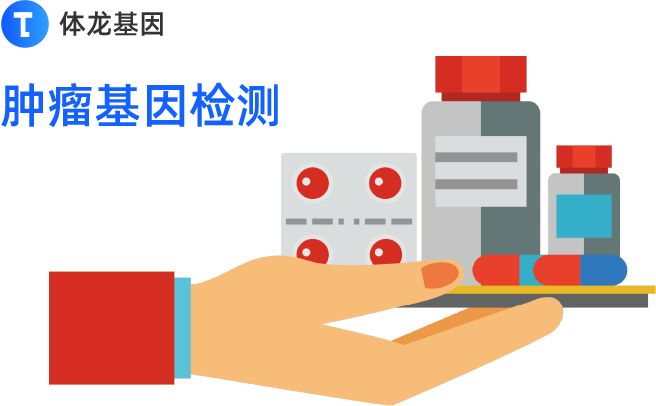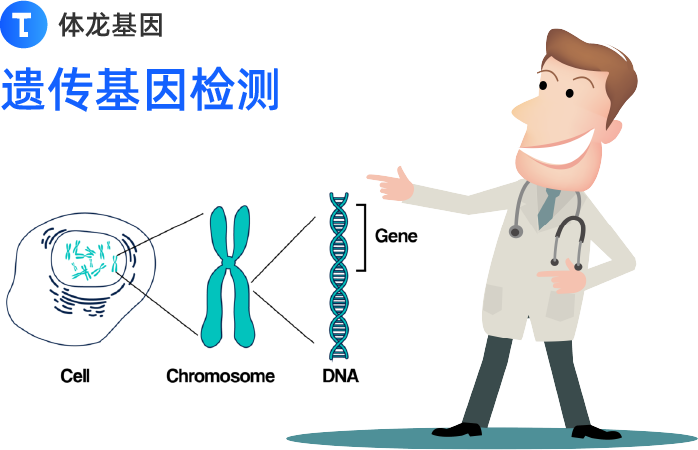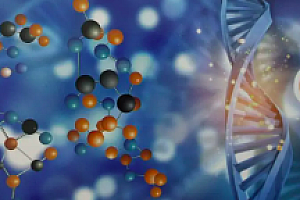近年来,国内高等学府门槛越来越高,据说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,一线城市的好单位对一个正高职位开出的条件是:一篇 CNS 文章或者两篇 CNS 子刊文章,外加 2~3 篇影响因子 10 分左右的文章。如果以副高(副教授或副研究员)入职,则需要工作 5 年,产出至少 2 篇影响因子 10 分以上的文章以后,才能申请升正高。这样的要求,换成十几、二十年前,可能超出两院院士的入选标准。
上个月底,我们单位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,报告人中有几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诺奖获得者,其中一位来自加大伯克利分校的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——Randy Schekman。Schekman 获得诺奖后干的一件大事,便是在《卫报》(The Guardian)撰文大肆抨击 CNS 三大期刊,批评它们带头用 “影响因子(IF)” 来衡量学术水平,搞坏了整个学术评价系统。这次他老也不例外,在报告快结束时话锋一转,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 “攻击” 了三大期刊以及它们所导致的 IF 崇拜现象。
其实,很多科研人员都明白,论文的影响与学术水平其实不是一回事。好的科研往往独辟蹊径,所出的成果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会慢慢被主流接受,在短期引用率上反映不出来。论文 IF 的计算基于短期(两年)引用,所以要追求论文的 IF,意味着我们必须做热点性、跟风性的研究工作。
事实上,崇拜高 IF 期刊是个国际性潮流,并非中国科技界所独有。但西方高校还是有一系列的机制来予以平衡的。比如在人事招聘和升迁中,同行评议结果具有非常高的权重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基金的个人介绍(Biosketch)格式就可见一斑,新版的格式不让你一味罗列文章和影响因子,而是让你准确地写出你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,每个贡献下至多列四篇支持性文章。
在这里,我不打算过多讨论期刊的 IF 问题,而是想说一个细思恐极的现象:很多人的科研人生,或者严格地说是全部人生——包括单位收入、住房面积、婚姻、孩子学校,甚至你的交通工具以及你碗里的红烧肉,都与你发表论文的杂志 “IF” 直接相关。也就是说,学者们把自己一生中的大事全部交给了那几个杂志社来决定。我们一直说的 “知识改变命运” 在现实中应该改成“论文改变命运”,或者更直接地说,你论文的 IF 决定了你的命运。
反过来想一想,其实杂志社只是杂志社,它们与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大关系,当我们找工作时,它们连封推荐信都写不了。
与 Schekman 观点不同的是,我并不认为这三大杂志社本身有啥问题,从商业办刊角度来看,它们追求高影响因子并没有错,况且它们的文章质量应该是同类中最好的。问题是我们有些科研管理者志大才疏,被少数几个自认为是科学精英的言论所蛊惑,盲目崇拜高 IF 期刊,主动伸出双手套进对方的 “镣铐”。
(责任编辑:sgx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