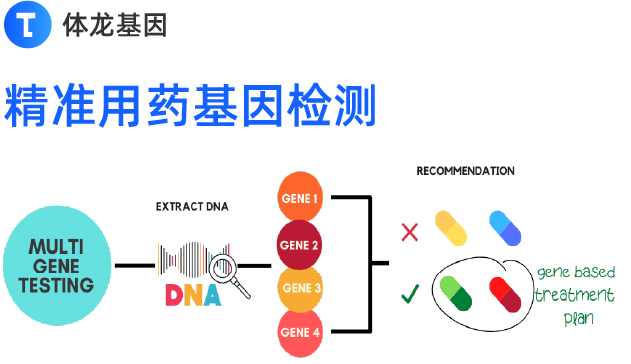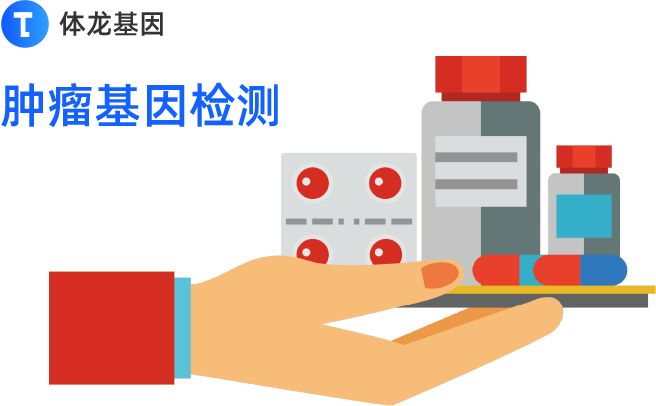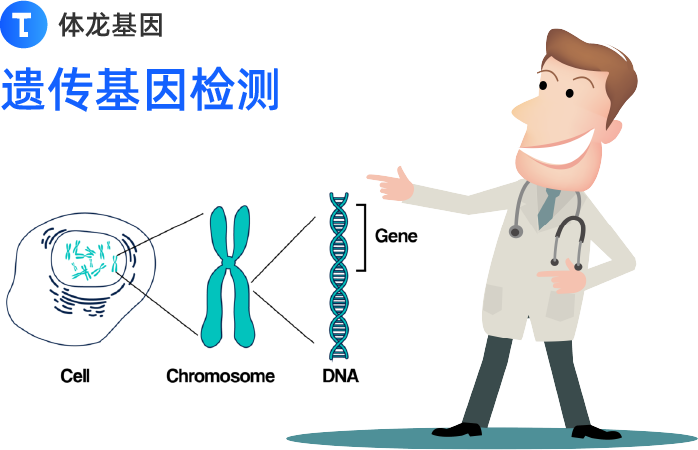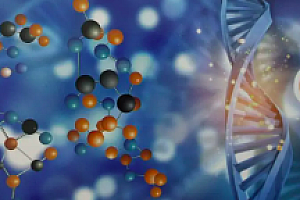原标题:慢新闻 | 在绝望的大海里捞希望的针
作家冯唐曾经是协和医学院的妇科博士,研究卵巢癌,但他放弃了:“我眼看着这三年跟踪的卵巢癌病人,手术、化疗、复发、再手术、再化疗,三年内,无论医生如何处理,小一半的死去……”
卵巢癌的临床和研究是医学各科里最没成就感的工作。
但疾病不会放过人。在绝望的大海里捞希望的针,都希望医生是那个天降的“神”,其实,有三个“神”。
手术室火力全开,医生小跑。
【手术室里的腹腔】
早上8点,重庆肿瘤医院17间手术室火力全开,走廊里说话都是2倍速,医生护士都在小跑,消毒,领药品,领器械,填各种表格,平常或者生死的一天开始了。
手术台上是42岁的女患者,腹腔打开,皮肤往下,脂肪层、大网膜、鼓成一个个气泡状的肠子、子宫、附件……能装下胎儿,装下生命的子宫,只有一个鹅蛋大,很快它会被超声刀和电刀切走,双侧卵巢也会切走。
腹腔刚打开的20多分钟,我一直觉得自己腹部有刀割的痛。麻醉师自己带了小音箱,在放《大悲咒》《十年》和《天天想你》。
主刀的医生黄裕,在妇瘤科带着一个组,这个组的研究方向是卵巢癌。
手术中的黄裕
电刀切除人体组织,有一小股青烟腾起,会散发焦糊的气味,黄裕切除卵巢,巡回护士马上装进标本袋送去病理科冰冻检验,30分钟后,护士会在手术室的电脑上查到定性结果,回复黄裕。
果然是恶性肿瘤。黄裕和两位助手已经开始清扫腹腔淋巴,没有意外,也无叹息,还能做手术的病人总比不能做的要好。
黄裕专注地盯着监视器为病人做宫腔镜手术
手术结束已经是下午1点半,黄裕回办公室扒了两口冷饭,然后填手术报告。下午两点还有一台手术。如果是周二,下午她是看门诊,手术没完就请同事帮忙先看着。“上午腿累,下午嗓子累。”
另一间手术室的主刀医生马丽芳,也在黄裕的团队里。她瘦,手臂像未发育少女般纤细,声音也细。手术一般连着两三台,一站一天,有时候中间来不及吃饭,只能喝少量水,“但是我从没昏过台。”她强调说。
没人专门穿防静脉曲张的压缩裤,几个小时下来腿都站在固定点位,没挪一下。黄裕说:“肾上腺素维持在高水平,都在手上,注意不到腿。”
生理期怎么办?妇科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做科普:“卫生巾两小时必须更换,否则细菌飙升”,轮到自己,都说“没办法,忍忍吧,总不能让腹腔敞在那里”。
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清点纱布、针头、瓶子、废线、剪刀、钳子,反复清点到第五次的时候,手术差不多就结束了,清点的声音是医生们的结束曲,比什么音乐都好听。
一台新手术,麻醉师正在为病人做麻醉。
【人间值得不值得】
卵巢癌死亡率占妇科首位,发病原因至今不明。因为卵巢位置在腹腔较深处,发现时几乎都为中晚期,70%已扩散,据医生们的实际掌握,三年存活率仅30%。
手术,化疗,复发,复发间隔一次比一次短,最后腹腔、胸腔大量积液,肠梗阻,死亡。活过5年,是惊喜,7年以上,是奇迹。黄裕跟踪的患者,最长存活12年。
绝境里的人怎样活,怎样死,病房是台全息记录仪。
广安的黄小平(化名)是黄裕的病人,2012年11月7日做的手术,5年多的时间里,丈夫老李带着她往返广安和重庆80多次,仅化疗就32次。妇瘤科6楼的医生和护士都认识老李。
65岁的老李可以按顺序准确地说出哪年哪月来医院,做了什么检查,指数是多少,用了什么治疗手段,用了什么药。往返广安和重庆,他们舍不得打车,都是坐大巴或者火车再换公交。他一个人背两个大包,黄小平身体虚弱,走走停停,他要一路搀扶。
有一次老李摔了膝盖,一瘸一拐,还是背两个大包,扶一个人。老李颈椎病发,站起来头昏得看不清地面,还是摸着扶手一步步挪着去医院:“她身体虚,办手续跑上跑下哪有力气。”
黄小平一说话就不停咳,说两句话鼻血就往外流:“我活着太受罪了,他也受罪……”老李说:“我只要她能活下去,一年都行,半年也可以,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黄裕经常给老李打电话,关心黄小平的病情,沟通治疗方案。“难得有情人,难得这样漫长的耐心和坚持。终究是在告别,那就努力让这场告别长一点,再长一点。”
老李坐在病床边守护着妻子黄小平
世上告别万千,另一种也在人间。
马丽芳在病房值班的一个晚上,一个宫颈癌晚期患者坐在轮椅上,被妈妈送来医院,流血不止。“通俗地说,宫颈癌晚期腹腔会漏,膀胱漏,直肠漏,尿液、粪便、脓血会漏进宫腔,然后漏出身体,会很臭,非常臭。” 病人的丈夫不愿意家里被污染,差不多算是撵着母女来医院。
所有医学手段都已经失效,病人知道要告别了。她跟马丽芳说,她想吃很多东西,这样,那样,她把自己爱吃的重庆美食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一遍,念完,人走了。
马丽芳是山西人,记不得那些美食的名字,只记得她转身出门就痛哭了一场。
女性宫颈癌的病因与男性密切相关。妻子在脓臭中死去,丈夫在清洁的家里。
黄裕目睹过一家人,女孩很小被收养,十几岁又住进男友家,二十多岁患病去世,亲生父母、养父、男友家都狠狠闹,最后的补偿,三家人要闹到法院来分。
“人间不值得”,疾病把人层层剥开给人看。
黄裕(右一)和助手正在做手术
【一种投射】
黄裕今年40岁,10年前母亲去世,肺癌。
她在给患者做后装(一种放射性治疗),电脑上方的墙上挂着辐射监测,显示2102。母亲是一处软肋,10年的时间还是不能释然,一说泪光就浮上来。
“我以前脾气不好,对家人尤其不耐烦,工作忙,一接电话就烦,回家累,更不想说话,家里人都要看我脸色。”母亲持续咳嗽,也不敢问她,自己跑去附近小医院照了片,没照清楚,就当普通肺炎治,耽误了治疗,一直拖到晚期。
她说母亲的死让她改变了对亲人的态度,包括朋友。中午手术结束,微信打开啪啦啪啦一串同学朋友咨询的各种问题,比如宫颈癌疫苗,比如担心黑色素瘤,找她摘除黑痣,她还没扒拉冷饭,就先一一回复。
黄裕的书架(受访者供图)
黄裕家里的跑步机基本都是用来走路(受访者供图)
马丽芳也烦妈妈在她没下班的时候打电话。她是80后,单身,看上去像个纤秀的大学生,一个人在重庆,妈妈总是会有各种担心。整个6楼没有一寸空闲安静的地方可以谈话,我们只能站在暂时没有患者的检查室里聊。
医生马丽芳
今天正是她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早上她的一个病人要出院,一个老人,宫颈癌。子女强烈要求隐瞒病人,坚持要出院。“经济原因吧,子女不愿意拿钱,这个疗程大约3至5万。医保报销接近一半。”她难过的是,作为医生,可以预见治疗的预后效果很好,但是要眼睁睁放弃。
“病人走的时候一直在问我:马医生,为什么我还在流血呀?”
“是不是看多了这种‘人间不值得’,所以也投射到你个人生活,比如觉得婚姻‘不值得’?”
“也不是,我觉得我是偏理性的。当然,妇科女医生,工作多少会让你对女性的境遇和命运有更多思考。比如,一个男人,爱护女性肯定是一个基本要求。”
不生育是卵巢癌的高风险因素,问她身为医生怕不怕?她笑着强调:“体检!体检!体检!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当然,每次拿体检结果的时候还是很紧张。”医院40岁以下的医生每两年体检一次,她说,你能不能帮我们呼吁一下一年一检?
马丽芳打电话为病人调药
【多活一个月】
春节前的最后一周,人间各不同,病房各不同。
一位60多岁的病人卵巢癌晚期,查房的时候,病人已经失去意识,有谵妄表现。很快人就走了。病人确诊一年,自己和家属文化素养、经济条件都不错,都很配合医生积极治疗,但是……黄裕说起也很惋惜:“疾病不会完全按照人间的逻辑来。”
中午的时候,黄裕以前的内膜癌病人来看她。病人已经出院5、6年,是位幼儿园食堂的阿姨,每到寒暑假,都会亲手做一大袋包子馒头带来看她。这次还带了一罐蛋白粉,在病人的理解中,蛋白粉吃了对身体好,她说让黄医生补补身体。每到假期,她把出门旅游的照片发给黄裕,发的人看的人都很开心。
黄裕见过最积极的病人,是一位早年当过赤脚医生的阿姨。“我们所有内部的业务学习,学术会议,她都要来旁听,认认真真记笔记,她要知道最前沿的学术成果,蛛丝马迹地寻找自己生的希望。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也拒绝助眠药物,她怕睡过去了再也醒不来。”
这位患者手术后活了7年。
“生命可能比宇宙更复杂,医生面对的一样是茫茫未知。”医生可能只是一个执灯寻路的人,更多时候,病人要做自己的“神”,爱你的人,也要做你的“神”。
“这个令人绝望的疾病和缺乏成就感的治疗,总要有点什么才能支撑?”
马丽芳说:“跟时间赛跑,卵巢癌的药品研发特别多。哪怕延长半年生命,哪怕多活一个月,就可能有新药出来。”
黄裕说:“如果以三年为线,我们努力给她有一定生活质量的三年,三年可以陪伴家人,完成心愿,期待奇迹,人人都会书写自己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”
医生查看病人伤口恢复情况,期待奇迹。
文图来自重庆晚报—慢新闻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: